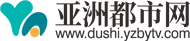文/展展
 (资料图)
(资料图)
编辑/艾略
杨丽萍又一次被争议包裹。
最新版本的《孔雀》中,舞蹈接近尾声,男舞者全身只穿一条肉色紧身打底裤,侧躺在女演员怀里。现场观众看得十分感动,被舞蹈所展现的爱、美与力量打动,赞叹男舞者的肌肉线条与表现力;但也有人抗议此段落低俗、造型不雅,甚至批评杨丽萍没有羞耻心。
《孔雀》中,男舞者的造型被部分评论指责不雅,图源:社交媒体
不算意外,这个备受争议的段落,恰恰是这支舞蹈中杨丽萍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它对演员要求极高,脱离了服装的包裹,舞者仅剩身体这一道具,只能借助最极致的肢体语言完成表达,它无限接近于舞蹈的本质。
事后,杨丽萍解释这一造型,当然是剧情所需:男孔雀在最后一刻把最美丽的羽毛奉献出去,以此让女孔雀获得自由。羽毛脱落,纷纷扬扬地飞起又落下。之后男孔雀还原到生命初始的样子,完成了终结与延续。这一表达还有更有深刻的意味,杨丽萍说,我们都是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走。
2022版舞剧《孔雀》,图源:CFP/授权使用
这一回应很“杨丽萍”:造型是为舞蹈本身服务;她一直以来关心且孜孜不倦探寻的,不过是美与生命本身。相较之下,“低俗”、“无底线”的批评显得浅薄又“上纲上线”。但凡看过杨丽萍的舞蹈,或对她稍加了解,都不至于这样大惊小怪。她向来是自然的崇拜者,此次男舞者的造型,也不过是对自然本身的又一次效仿。
一直以来,她最基本的舞蹈观是:出力,每个动作要像从地里长出来一样。基于这样的理念,相比排练,她更愿意让舞者们从自然中获得启示,鼓励他们模仿植物生长,动物交尾,风拂过叶子引发的轻轻颤动;她对翻飞、劈叉、高举的基本范式深恶痛绝,年轻时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后,便迅速地知道踮着脚尖跳芭蕾“不是我的语言”,立即离开了。那时,团员们对她最多的评价是:“一点技巧都没有,腿都拉不直。”
杨丽萍年轻时(资料图),图源:网络
杨丽萍的难得在于她“难以效仿”,连身上的争议也是
杨丽萍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过往几十年接受采访,所说的话几乎没变过。《云南映象》的合作者之一殷晓健这样形容杨丽萍“话少而天真”。但与此同时,她又是审美极好的、坦荡的、无所顾忌、极其敏感的,对自然中发生的一切“特别有感觉”。
2012年,《天下女人》节目现场,杨丽萍带着侄女小彩旗接受采访,主持人问起杨丽萍对小彩旗学习上的要求。小彩旗认真回答:“她就是经常让我自学,然后多看一些书,她有时候也会让我背诗啊什么的。”
杨丽萍的反应却是:“那我让你看树叶在阳光下被照得闪动你怎么不说呢?”如同艺术家与好好学生之间的gap,杨丽萍在乎的是生命体验,接收者费力总结出的却是方法论。
节目中,她一边说,一边举起一只手,白色的修长的指甲,仿佛阳光下亮闪闪的树叶,轻盈生动,很快,她将手轻轻向下拨,仿佛鸟儿拂过水面,“我告诉你说小燕子划过水面它留下什么了?其实你就没记住这个,所以你到现在都没感觉到一朵花开放是什么感觉。”
她自称生命的旁观者,曾骄傲地宣扬:“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享受,有些是体验,有些是旁观。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
这使她的舞蹈难以总结和效仿,因为生命力本身是难以效仿的,更多是顺从天性,是什么样的土结出什么样的花,是一片叶子长出另一片叶子。她是天生的舞者。她的舞蹈之所以打动观众,不在于她的腿踢得多高、身体多柔软。她的舞蹈从来不是哗众取宠或炫技,而是动作之中包含无数流动的细节与气韵,每块肌肉各有各的语言。
这样一个人,一辈子都在研究孔雀。“孔雀”几乎成了她身上的一个“符号”,类似于天鹅在西方舞中的地位。孔雀太美了,尤其是孔雀交配的时刻——她对性从来不隐晦,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讲到《雀之恋》,她坦荡地说:“我觉得性是特别自然的事情,所以这段舞蹈并不避讳这些。”她细细描述过那样的场景:慢慢展开尾巴,尖叫声如同轰鸣。
一辈子,她都在用身体的语法诠释孔雀。孔雀与孔雀的互相引诱,孔雀的老去与死亡。还有这一次,孔雀奉献出自己的羽毛,给另一只孔雀。
倾注杨丽萍多年心血的孔雀舞,图源:CFP/授权使用
倾注杨丽萍多年心血的孔雀舞,图源:CFP/授权使用
杨丽萍向来对自己的舞蹈向来追求极致精细的把控。从灯光、音乐到服装无不如此。《三联生活周刊》记载过这样一个细节:2012年,央视春晚彩排,到了《雀之恋》,杨丽萍安排两个舞蹈演员在台上替她做动作,她在下面盯着摄像机,和导演一起商量镜头怎么办。她拒绝惯常的晚会镜头移动方式,坚决地要求按照她的方式来。
对她而言,跳舞是在与神交流。孔雀附身,于是会有灵魂飘荡、忘记四肢的时刻。可叹的是,看客们关心的却是被这个灵魂附着的躯体,是否穿着得体。
这真是一种天大的误读。一种夏虫不可语冰的悲哀。是在跟一枚月亮谈六便士。是用被桎梏的脑袋去碰撞天性,企图用同样的框架桎梏她。
这不是她第一次遇到类似的困境了。上一次,有人在她的短视频下留言:“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留言让人哭笑不得。仿佛她在舞蹈上成就再多,跳得再远,也离不开没有孩子这个圈套。
杨丽萍曾被网友评论“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
围绕在她身上的话题不该是这样的。
去年,杨丽萍解散了《云南映象》和《阿鹏找金花》两个团队。那时她出来接受媒体采访,话说得很直白:“没钱了嘛,发不了工资了。”她已经64岁了,从艺超过50年,她开始介意自己在镜头中的形象,特意嘱咐拍摄她的摄影师,不要拍得太近,不要给特写,“因为年纪大了,老了,不能拍特写。”这是美丽的舞者对外在形象的维护。
但与此同时,她对衰老又很坦荡。她曾在提到《孔雀之冬》时,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我的生命现在处于冬天,谁的肉体都会衰老,但我并不会恐慌,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意义。”
60岁的杨丽萍,肢体背影还保持舞蹈形态
面对这样一位舞蹈演员的衰老,本应值得庆幸仍可以看见她的演出,看一场少一场。但此时,有人却一遍遍要求她出来自我解释。
当“三观党”占领评论高地,艺术被要求“自证清白”
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样了,人们用世俗观念框架里的“三观”去衡量文艺作品。《包法利夫人》的女主角被批评爱慕虚荣、主动投怀送抱;《丑小鸭》成了宣扬“血统论”,《海的女儿》则被视为不折不扣的恋爱脑故事,《泰坦尼克号》的主角Jack是小三,连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家有儿女》的小雪都被视为对待后妈态度不妥的“杠精”。
站在道德高地上去审判文艺作品,保守又保“洁”,这是一部分看客最容易、最可行的掌握评论话语权的方式。只要不符合“三观”,那一切都莫谈;只要穿得不够“得体”,便是伤风败俗。
或许,通往艺术的道路充满门槛,将它们拉下神坛更省事一些,三观和所谓“底线”是确定的标尺,让看客们觉得安全、可靠、有话可说、高高在上。于是,一条条规范建立起了我们审视的藩篱,最好全世界长一个样,穿一样的衣服——最好不要穿leggins(紧身裤),别以为它只是一条裤子,它那么贴身,真不得体;留一样的头发,最好每个作品中的人物从外观到心灵都完美得无可挑剔。否则,我们脆弱的心灵和眼球就会被污染。艺术突破藩篱的每一步都需要勇气和代价,但是倒退的一瞬间却可能只需要几声嘈杂的评价声。
早在几十年前,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裸体一旦成为艺术,便是最圣洁的。道德一旦沦为虚伪,便是最下流的。勇敢地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被世俗的流言蜚语所困扰。记住,要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
年轻时的舞者杨丽萍(资料图)
杨丽萍不该也不需要被放置在这样的衡量标准之中:生孩子、自证清白。好在,她也不在乎这些。她早就通过创作奔向了自由,从未因外界声音改变过自己。
早年《雀之灵》不被看好,舞团不替她报名参赛,她就亲自骑着单车将录像带送给评委会,早已过了截止期,对方答应她在评委休息时放给他们看。结果,《雀之灵》成了那年全国舞蹈大赛第一名。制作《云南映象》时,投资伙伴不出钱,国内舞蹈界基本不接受她的舞蹈,认为未经训练的少数民族上台是个笑话,她坚持自己的做法,这是她驾驭大场面舞蹈的开始,里面同样有性的表达。《两棵树》是少数民族的性舞蹈;登上春晚的《雀之恋》,与她合作的是现代舞演员王迪。她所创造的,既不是纯东方的,也不是纯西方的,朋友因此笑称她是“后现代孔雀”。
一直以来,她都在寻求突破,但一直以来,她所追求的未曾变更:舞蹈应该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就像她那些服装仿佛长在她身上,她的舞蹈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因此具备无可比拟的生命力与灵魂。就像月亮被人类歌颂或者诋毁,都不会更改它的光辉。她用力腾跳,早已突破了身体的限制,轻轻跃上高处。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平台观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