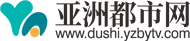接吻是一桩无数人都在做的小事。但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我们习惯用亲吻来表达爱意?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接吻是西方的外来习俗吗?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接吻只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古代中国人并不接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相比于接吻现象在日常中的司空见惯,接吻问题却是学术边缘中的边缘。 在最近出版的新书《接吻的中国史》中,就特意将“中国人的接吻”作为文化史问题进行探讨,做了史料性的实证研究。
作者从先秦古书、出土文献中寻觅证据,在汉墓画像石中找出图案,探讨闺房私密的卿卿我我,剖析中古骈俪的宏大制作,又于诗词、散曲、小说、笔记中一一拈出例证……说明,中国人对于接吻虽然不那么热衷、那么高调,但我们也自有中国人的“吻的文化史”。
古代中国人的接吻行为一直蒙着神秘色彩。就以古时形容接吻的语词为例,便有“呴”“呜”“接唇”“亲嘴”“做个吕字”等数十种之多,有的颇不容易立刻明白。从接吻这件小事的“前世今生”入手,我们却也可以看到古人的生活与世界。
撰文|重木
“接吻”是一种本能吗?
曾经著有《现代学林点将录》和《陈寅恪诗笺释》的胡文辉先生根据其平日里“随时留意,有闻辄录,积久成多”的史料,写了一本关于传统中国“吻”的小史。这部小史主要是以“史料排比……大体只是做出一个文化史的综述”,而非法国式哲人形而上的“玄虚想象”,但也恰恰如此,我们能够通过这部小史中丰富的文献资料,发现一直以来在被各种“天理”“为国为民”的宏大概念和叙述笼罩之下,古人在个体的、私人的亲密关系中的生活幽微之处。“吻”看似小题,但其背后又确实牵连着庞大且错综复杂的线索与背景,不仅有趣,也颇有意义。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接吻”看似一种人类的自然本性,中外古往今来应该也都在“无意识”地实践着,也正因其具有的某种“普遍”和日常性,而导致现代人与现代研究几乎对其视而不见,仿佛桌上的信。但当它在近代随着各种性学与生物学的发展而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时,接吻这一行为开始被看作是一种个体的生物性本能。在《并非本能:接吻的一般历史》这一章中,作者便通过对各类性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中对于接吻的解释,指出接吻“不是一种先天的本能,而是一种后天的习俗”,尤其是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西方流行文化在好莱坞影视等娱乐媒介的宣传和推波助澜下而渐渐地被认为是某种自然而然的“欧洲式”接吻,也“并非天经地义,而实为一种文化建构”。
更进一步,作者总结道:“指出接吻是一种文化建构,意味着的是:接吻作为一种初级性爱方式(前戏之前戏),并不是自然性、本能性的行为,而是后天习得的,即带有习惯性、风俗性的行为”。而也正因此,古今中外的“接吻”就必然因其所处的具体地理、文化和时间的差异,而会出现不同的形式以及对此形成不同的理解和观念。《接吻的中国史》主要研究的便是传统中国隐藏在各种文本和资料缝隙里的“吻之文化”,尤其是围绕着这一行为所建构起的庞大象征体系与实践,虽然这一文化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隐藏与遮蔽。
《接吻的中国史》,作者: 胡文辉, 版本:后浪|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6月
在近代中国西化的过程中, 作者发现“中国人是否接吻”成了现代化 (西化)问题中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而“接吻”这一被看做是“西式的/现代的”行为也随着人们的关注而渐渐在20世纪初的中国被关注。或也正因此,许多人才会以为“中国人的接吻,只是承受了西方的影响,中国人过去是不接吻的”,如张竞生便在其《接吻的艺术》中认为中国人对接吻“或偶一行之,但并未讲究与普遍实行”,但其后如周作人、叶灵凤等人都通过对传统一些文献或是日常生活的观察反驳了这一说法,认为“接吻”在中国自古有之,且“东方人是比西方人更了解的”(叶灵凤)。
在某种程度上,张竞生和周作人等人讨论的“接吻”既是同一件事,又不是一件事。张竞生所谓的“接吻”是“西式的”,是“巴黎,法国人的风尚”,而在其背后所牵涉的不仅仅只是两个个体的嘴唇相触,它还关联着这一行为背后更加复杂的观念模式,尤其是近代“欧洲式”接吻意义本身也经过历史的演变与发展;而周作人等人讨论古人的“嗅,我们乡间读作hsoong(西用切)”则在另一套认识论系统中运作与被赋予意义。
接吻是“西化”的习俗吗?
我们可以借用After Eunuchs的作者姜学豪(Howard Chiang)的“认识论现代性”(Epistemological modernity)概念来讨论这个问题,即“接吻”这一实践和行为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必然存在,并且在各类文本中也留下了书写与描述,但无论是“嗅”、还是之后胡文辉发掘出的“呜”“做个吕字”“亲嘴”与“接吻”等词汇,它们与民国时期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接吻”(kiss)早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东西,其背后便牵涉到认识论问题,即今人对于接吻这一行为及其意义的认知已经和古人存在差距,即使使用的词汇依旧,但其背后的庞大象征系统却早已经物是人非。
而关于古人“接吻”的文献资料,也往往处于一些相对于正统文献十分边缘的位置,除了胡文辉对咸卦的新意解读之外,早期有关接吻的文献大都来自房中术书籍(以及受其影响的汉画像石),而或许也因为房中术在秦汉时期的风行(“秦至中古时期视为房中术定型的阶段”)而使得这一通过规范男女性行为而达到养生与神仙目的的文本中包含着大量关于接吻的资料。也正是通过对这些房中术文本里有关“接吻”话语的归纳与分析,作者总结出中古以前古人对于接吻的两大认识:一是在古代中国,接吻是完全存在的,但却是“从属于性行为的一部分,只限于在私密状态中进行”;二是古人之所以重视接吻,目的是为了达到采阴补阳的养生效果,因此接吻又从属于房中术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古以前,接吻主要是性行为和房中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往往是私密的,在公共场合以及面对公众的文本中,便几乎难寻踪迹。
房中术对男女性行为的操作与实践有着巨细无靡的规定与限制,性交的目的在于采阴补阳以求长生,而非为了性行为本身(见李零《古代方术考》中对房中术的研究),因此接吻也就具有特定的目的性。房中术中对接吻的理解和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传统中国关于接吻的最重要认知框架,一直伴随着房中术的发展而存在于世,并且在房中术于中古后期进入没落或是辗转进入明清艳情小说中后,它也暗度陈仓地开启了新的场域,在明清大众与通俗文学中获得了新生。
在《不登大雅之堂:诗词曲歌举例》一章中,作者便强调伴随着房中术文本的没落,接吻再次转入私密,与此同时也在一系列不登大雅之堂的边缘文本中出现。首先便是自古以来就被认为用于“言志”的诗(往往是区别于古诗的新体诗)成为描述接吻的载体,但往往这些艳诗本身也属小众,且大都难以传世,所以胡文辉所能发现的相关资料也十分有限,而其中以《十香诗》和清人孙原湘的《个人》最为经典;而除了诗,被认为出自青楼歌伎的词以及其后的元曲和各种民歌,也成为描写接吻的主要文学载体。“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曲又更下于词,而民歌、小调又更下于曲”。
这三类文体的共同特点都是属于“小技”且边缘,也因此在面对主流规范时有更多的余地和空间描写私密情感、情欲和行为(“对大人先生视为鄙俗的成分也更能容纳”),尤其是在通俗且大众的民歌里,依旧具有强烈的“野性”,相比较于文质彬彬的诗文所关注的国民大事,它却收藏着普通民众更加多元、活泼且旺盛的情感、情色想象与欲望。所以这也是《接吻的中国史》中能够收集到的最多的相关资料,可以和明清时期的艳情小说一较高下。
《恋恋红尘》,作者: 李孝悌,版本: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0月
明清时期,世俗社会大开,红尘滚滚,就如李孝悌在其《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中所指出的,明代商业的高速发展带动城市化进程,再加上阳明后学对于个体人欲与人性的张扬,而使得明清社会繁花似锦、欲望横飞。而诸如汤显祖的《情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醉西湖主人的《弁而钗》与李渔的《肉蒲团》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诞生,其中涉及的男女/男男情爱行为令人眼花缭乱,接吻也自然就是题中之义。就如胡文辉所言,“中古以前,房中术在社会上影响较大(与神仙观念的影响成正比),但可能也仍限于上层阶级;至中古以降,旧贵族阶级解体,大众社会更为壮大,而房中术亦随之式微”,也正因此,房中术中关于性的各种神话和伪科学渐渐被俗世的、自然主义的性取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房中术同样以一种改头换面的形式进入了明清艳情小说的性描写中)。
而也正是在百花齐放的艳情小说中,“接吻”——或以当时最常用的“亲嘴”一词——的各类用语被重现与整合,并且还影响到如日本等周边国家,如“做个吕字”这样隐指接吻的用语。而同样出现在明清艳情小说中的“接吻”一词,根据考证,或许也是由中国传入日本后,被日人用来翻译英文的kiss(吻),然后又在晚清民国时期传回中国。而其“出口转内销”的经历也并非个例,而是近代中国用语和词汇上的一个典型特征(见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我们或许也可以通过“接吻”这一用语的复杂跨国经历来进一步说明,那些看似未变的用语背后其实已经遭遇了完整的认识论颠覆,而当它留学归来之后,这一融合着不同认识论的词汇将再次遭遇不同观念的碰撞。在来去之间,不同的认识论和观念已经融合,而远非传统中认为的某种文化对另一文化的彻底殖民,更真实的情况或许就是霍米 ·巴巴所谓的“杂交”状态。
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因如何处理口臭而引起的关于古人如何洁口问题的讨论中,尤其当我们过分执着于讨论诸如牙签、牙刷到底是哪个国家发明时(胡文辉指出,“牙刷是中国人大约在北宋时创造的,但仍未普遍,至南宋时则成为大众的日常用品”),往往忽略了背后更加复杂的“来-去”这样反复且彼此影响的过程。从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土的杨枝刷牙方式,到古人由此启发或是对这一行为的进一步改善而发明的牙签与牙刷,文化之间并非总是“殖民-被殖民”这一对立的二元模式,而更多的是一种彼此影响而最终成为一种“杂交”的模式。
《暮光之城》电影剧照。
“性爱之吻”缩小了接吻的广阔意涵
在《东是东,西是西:与域外的对照》一章中,胡文辉通过对比中西传统中“接吻”意义的改变指出这一相同行为背后可能因社会文化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理解,尤其是西方“接吻”具有的“宗教-礼仪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单纯性和公共性,使其区别于后来发展成的“恋爱之吻”以及传统中国的“性爱之吻”。而在“接吻”东来的影响中,其古老的礼仪模式始终未能被其他地方接受,反而是作为恋爱和亲密的象征被普遍接受。这也再次说明,不同文化在相遇后,往往会受制于本身的认识论框架,因此即使一方再过强势,也很难令对方完全全盘接受。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彼此斗争和协商的动态过程。
在东西对比中,作者认为“对于接吻的态度,中国人本来并没有什么不正常,倒是西洋人比较不正常而已”。在这里,作者预设了一个何谓“正常”的标准,即——在他看来——接吻作为性爱的前戏是属于正常的,因此西方传统中的宗教式礼仪性接吻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性便是“不正常”的了,但这一推断恰恰与作者在前面指出的“接吻是一种文化和习俗的建构”相悖。因为在传统西方中,接吻或许不仅仅只是作为性爱的前奏,甚至它更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象征意义是代表亲密或是具有特定的宗教内涵,因此对于西人而言这便是接吻的正常意义,和传统中国的“接吻”相比,具有差异,但却不存在正常与否——判断“正常”总是带有规范性目的,同时会具有等级、道德和意义高低的判断。
在某种程度上,被作者认为是正常的传统中国的“性爱之吻”可能恰恰缩小了“接吻”或许能够具有的广阔意涵——当然,这也与不同文化对这一行为意义的建构有关。我们会发现除了西方的宗教式礼仪之吻外,像一些国家——如泰国——也会亲吻君主的鞋子,以表达崇敬。所以,亲吻这一行为可能具有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意义可能性,但随着西方“恋爱之吻”的强势以及其在各种大众文化中的传播,接吻的意义被迅速地收缩,而开始仅仅与爱人间的亲密行为有关,虽然一些地域和文化中依旧存在着如亲吻面容、手背和鞋面的行为,但也已经置于边缘了。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毛诗序》中曾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个体的情感表达往往会通过身体的不同举动来展现,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现,在欣喜或悲伤等情绪中,人们会用亲吻来表达对对方喜悦的分享或是安慰。当然,这一行为或是同样来源于“西式”接吻传统的演变,但这一行为本身却具有自身的意义,一种不是被外在强加而是某种“自然”的身体行为。这个问题似乎再次回到了《接吻的中国史》第一章讨论的“接吻是否是本能”的问题,我们身体的某些行为和举动必然是文化潜移默化训练的结果,但感觉的直接性同样值得关注。
讨论感觉的直接性不是为了重回“接吻”是否是本能的滥调,而是为了强调对于“接吻”的文化和意义的建构本身是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无论是“近代以前,中日一直是性爱之吻”,还是西洋“经历了从宗教时代到世俗时代的变化,最终定型的恋爱之吻”,它们或许都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接吻这一行为对于个体或人类的多样性可能与意义的绽放。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本有趣的著作的基础上,去进一步思考“接吻”的可能性。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重木;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封面题图素材来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 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全年合辑!2022《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合订本来啦!
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