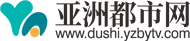随笔 | 斯人竟不起,惆怅意无穷
亲爱的《社会科学报》读者,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满足大家对本报的阅读需求,我们准备了一份问卷。参与填写,将有机会获得2024年《社会科学报》赠阅。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问
卷
▋ 随笔
二十多年过去了,夏仲翼老师以九十二岁高龄离世,未尝不是“知免”全归的解脱,甚至是某种“ripeness is all”的圆满。
原文:斯人竟不起,惆怅意无穷
作者 | 北京大学 张沛
图片 |网络
2023年5月28日上午,我起床后一眼看到高俐敏师母在清晨发来的微信“仲翼走了,今天4点40分”——夏老师自5月8日住院治疗以来,病情几经反复,我已有一定心理准备;然而事情发生,我仍然感到巨大难言的悲伤:我的老师终于还是走了!
开启我国翻译、研究巴赫金的先河
夏仲翼先生1931年11月19日生于上海,早年入读沪江大学英文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沪江大学英文系并入复旦大学。先生转入复旦大学后,在程雨民先生建议下,由英文专业改读俄文专业,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除1955—1956年在上海船舶设计院做了约一年的翻译工作外,在复旦俄文系一直工作至1963年。后应国家国防人才培养需要,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担任俄文教员。1969年复员转业后回到上海,1970—1978年在上海探伤机厂当工人。1978年高校恢复招生后,调回复旦外文系任教。夏仲翼先生长期从事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开设过 “欧美文学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潮流”“当代苏联文学进程”“俄罗斯长篇小说”“外国文学理论及文艺学方法论问题”“欧美小说艺术研究”等一系列课程。先生主讲的课程,注重清理文学史材料,并加以理论归纳,观察细致,见解独到,因而深受好评。
夏先生在教学科研之余,还从事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译有苏联当代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国家奖获得作品 《鱼王》《牧童和牧女》,叶·扎米亚金的 《小城轶事》,雷巴柯夫的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长篇和中篇小说。1982年8月25日,夏先生翻译的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在 《世界文学》上发表,开启了我国翻译、研究巴赫金的先河。
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师生缘
我从1996年秋季开始追随夏仲翼老师学习欧美文论,由此正式缔结师生之谊,迄今已近27年。可以说,这段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师生缘分已经沉淀、融化为我生命记忆和学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间种种,一言难尽,不过我想可以先从当年选修夏老师为我们外文系1995级研究生开设的第一门专业课“20世纪欧美文论”讲起。
当时,我的兴趣主要在文学方面,那时尚不知晓“文学”是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位一体的存在,对理论感到隔阂。不难想见,我在当年“20世纪欧美文论”课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最后课程论文成绩只得了84分——这是我在复旦学习期间取得的最差成绩之一。1998年4月,夏师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向由贾植芳先生、陆谷孙先生、陈思和先生组成的三人答辩委员会介绍学生情况,说到“张沛同学选修了诸多课程,成绩优”时,他瞥了一眼手中的成绩单(我想他当时一定看到了这个84分),略有思忖,然后加重语气说出下一字——“良”。成绩“优良”,而且主要是“良”,这无疑是一个公正的评价。对于夏老师的学术判断,无论是当初给我84分的成绩,还是他后来在答辩会上强调指出这一点,我都感到心服口服:真正的学者和老师,不正应该这样行事吗?
十多年后,我指导的一名硕士生从牛津大学暑期访学归来,向我介绍她的选课学习情况,并特别解释了其中一项69分的成绩:牛津和剑桥大学传统上70分即属优秀,因此69分在中国学生已为难得云云。我当时联想到夏老师给我的84分,向她回忆和讲述了这段往事。事实上,近二十年来,我在北大目睹了学生成绩因内卷而导致的通胀(同时也是缩水),特别是一些教师为了招徕学生、扩大影响而采取的高开高走政策,甚至自己有时也未能免俗。对比夏师当年的做法,我不如我师,可以无论矣——不过我希望下一代学生能做得更好,至少不是更差。
聊学问,他很开心
我毕业工作后,但有机会来沪,必来武宁新村看望夏老师和师母。不过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屈指算来只有四五次。每次来访,老师和师母都热情接待,有时夏韫兄也特意赶来聚会,令人感念。每次我们师生之间都有敞开心扉的交流。如2018年5月底我第三次来上海看望夏师,夏师和师母说起夏老师在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工作期间(1966—1969)及他们在1976年秋的家庭往事,让人感慨动容。特别是2020年11月底最后一次看望老师,此前师母曾告我夏师近年记忆和语言能力严重衰退、大不如前,我来时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不料我一进门,夏老师听到师母通报“老夏,张沛来了!”便径直迎了出来,而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张沛,你怎么好像长高了?”——老师完全记得我,只是他自己不复当年的壮硕身形,甚至比两年前我来看他时又清减了不少,师母在席间笑说夏老师现在“真成了一个老伯伯了”,因此他见到我时可能回到了当年的印象,才会产生我“长高了”的错觉。尽管如此,夏师的神态举止依然温厚从容,特别是当我向他汇报近期的写作和出版计划时,他的目光瞬间变得专注清明,并在听完后认真地点评说:“这个题目很好!”在我记忆中,这是夏老师第二次夸我。这一刻,我既感自豪,又有些难过,还有一丝欣慰。中午饭后,我辞别夏师和师母,相约明日寿庆会上再见。夏韫兄开车送我至华师大出版社,途中他欣然告诉我:“爸爸今天状态不错,平时没有这样精神。你和他聊学问,他很开心。”我听后悲欣交集,无言以对。
二十多年过去了,夏老师以九十二岁高龄离世,未尝不是“知免”全归的解脱,甚至是某种“ripeness is all”的圆满。尽管他的家人和朋友到底意难平,可是也只能存乎遐想和付诸沉默而已了。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9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拓展阅读
随笔 | 冥想或让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更深
阅读 | 《广岛札记》:散发着人道主义光辉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