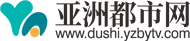陈彦
陈彦新作《星空与半棵树》
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本身就是哲学的两面,仰望星空正是为了更好地脚踏实地。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
小说的开头是一幕来自猫头鹰视角的舞台剧,它目睹了一棵长在两家地畔子中间的百年老树被连根挖起,随即被贩卖到都市,不知去向……著名作家陈彦新作《星空与半棵树》的故事,由此开始。
作为拥有半棵树产权的温如风,踏上了寻找自尊与公义的道路;而热爱观测星空的小镇公务员安北斗,被安排了“观照”温如风的工作。在一场巨大的时代变革与演进中,我们既仰望星空,又努力去倾听小人物的诉说。
从舞台到更大的“舞台”,从“舞台三部曲”到《星空与半棵树》,陈彦说,在写《喜剧》的过程中,就已经萌发了《星空与半棵树》的写作欲念,这个“转向”是自然发生的。“一切从生活出发,也努力表达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生态主义与象征主义的情愫。”陈彦说。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创作有了一个怎样的转向?
陈彦:《星空与半棵树》是有别于“舞台三部曲”的一个新长篇,有别指的是它所用的材料和叙述的方法有别。《装台》《主角》《喜剧》是从舞台人生的角度,拉开社会的更多面向,看似聚焦演艺人生,其实也是在讲述人间百态。而《星空与半棵树》是从乡村、城镇、都市,农民、公务员、职员,家庭、家族、婚姻、爱情,科学、自然、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去打开一个丰富的现实世界,充分展示我所想书写的广阔的现实人生。
中青报·中青网:从某种程度来说,《星空与半棵树》无论从标题还是内容,都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结合。当你听说半棵树的故事后,为什么想到和星空一起写?“半棵树”与“星空”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陈彦:是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本身就是哲学的两面,仰望星空正是为了更好地脚踏实地,而要做好脚踏实地,又必须仰望星空,从而找到脚踏实地的理由,否则,脚踏实地可能会踏得毫无价值。只有辽阔的视野与较高开放度的思维,才可能养护好我们的脚踏实地。
当我第一次听到由半棵树归属权所引发的一连串矛盾时,脑子中立即出现了一个十分微末的东西与一个十分博大的东西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的对照所打开的是十分广阔的现实和精神空间。如果眼光只停留在半棵树上,小说可能写得很窄、很小、很闭锁,也就毫无意义。
无论“星空”还是“半棵树”,都是在努力洞穿人与自然、人与人际、人与自身的复杂结构与精神隐秘。“半棵树”与“星空”,其自身就象征着小与大、窄与宽、薄与厚、轻与重,夏虫、山泉与雷鸣、惊涛之间的复杂而辩证的诸种关系。而在这些关系中,蕴藏着理解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隐秘通道。
中青报·中青网:安北斗迷恋星空,温如风为“半棵树”的权利问题诉求不歇,如何理解他俩最终“殊途同归”?
陈彦:温如风是一个勤劳的农民,他爱家庭、爱老婆、爱孩子,风里来雨里去,就是为了过好小康人家的生活。他也是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他的小康生活包括做人的尊严,是个面子和里子都要的人。因此,他就显得“轴”一些,在半棵树的权属上有点分寸不让的感觉。
可话又说回来,面对孙铁锤这样的村霸,没有温如风这样的“一根筋”也不行。公平、公道、正义是需要有人去呼唤的,温如风就是那个死不回头的呼唤者。可能有点讨厌,但他有自己的逻辑与道理。
安北斗始终就为他的“半棵树”所有权“耽误着青春”,俩人是同学,又是“猫抓老鼠”的“对手”,但其本质属性仍是殊途同归的“道友”——在维护公平、公正和人的尊严上,他们身份不同,处境也异,但观念是相通的。安北斗情愿放弃自己的前途守护温如风,体现的正是作为基层公务员的责任担当。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中安北斗、南归雁是基层公务员,可以看见他们的不易、无奈与坚守。现在有大量大学生正走向基层,他们也许有着同样的志向和同样的迷茫,你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陈彦:安北斗是最基层的一个小公务员,他在上大学时爱上了天文学,喜欢仰望星空。他所工作的小镇,由于远离城市,也的确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星空观测点。因此,他始终没有丢弃这个爱好,并且还在浩瀚星空中,希望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小行星发现,以及命名权,这是他仰望星空的巨大抱负与理想。
然而,脚下要做的具体工作又充满了鸡毛蒜皮的乡土与灶火气。地上的事都没搞明白,还仰望什么星空?这甚至遭到了包括老婆在内的诸多世俗的嘲弄与唾弃。小老百姓温如风半棵树的权利追诉问题,又让他全面负责。理想与现实、脚下与远方的浓烈诗意与厚重生活,便交织出无尽的浪漫、无助、焦灼,甚至荒诞,可他又始终坚韧地维护着一个小老百姓利益诉求的上达通道。
南归雁也是一个基层公务员,他怀揣巨大抱负,力图有所作为,想把一个镇“点亮起来”,开发旅游,但事与愿违,想干事反倒没有干成事,最终在反复试错中获得生命与精神的螺旋式上升。当他重新归来时,星空与半棵树的启示,让他对脚下的土地有了更加实际的把握,也有了发展生态旅游的新思考和新选择。这是一个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奋发有为、不畏艰难、与时俱进且最终有所作为的青年干部形象。
基层是最锻炼人的地方。一个有志于投身时代和社会事业的人,应该了解中国社会基层,那里能获得漂浮在上面永远也获得不了的东西。我永远怀念自己25岁前在乡村、城镇的生命实践与记忆。
中青报·中青网:书中有许多关于星空/宇宙的知识,你是一个天文爱好者吗?你从星空中获得了什么?
陈彦:我算是一个天文爱好者。天文学的根本是观测,科学的根本是实验。仰望星空其实就是观测。人类由对星空的好奇与观测,知道了自己渺小的方位,从而也知道了宇宙的无边无岸,并从恒星、行星、太阳系、银河系这样一些无穷大的构造中,懂得了万有引力、相互作用、相互制衡、彼此成就也彼此吞噬的秘密。
我们处在浩瀚宇宙看来可以忽略不计的一颗小星球上,也可以说是一粒微尘上,要懂得敬畏自然,也要庆幸我们的生命来之不易。就人类的观测看,还没有发现地球以外的生命迹象。因此,人,是最可宝贵的生命。文学刚好就是写人的,我们从星空中获得的一切信息,说到底,都是为人类服务的,服务今天,更服务未来。
中青报·中青网:舞台是你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非常熟悉,那对于《星空与半棵树》的发生地点、各色人物,你的个人经验是什么?
陈彦:那仍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块领地。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一直与农村与小城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即使在大都市工作,也时常会行走在乡间的田埂上。那里有我的亲人,更有我时常想回望的生活。加之在文艺团体做编剧、搞管理时,几乎走遍了大西北的山山水水,那里的星空与“半棵树”的诸多意象,都牵绊着我的内心,让一个写作者有无尽的景色想描绘,有荒凉的,也有斑斓的;更有无尽的故事想讲述,有悲催的,也有奋进的,是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中青报·中青网:书中有一个特别醒目的小动物——猫头鹰,为什么选择它的视角来叙述故事?
陈彦:这部小说除了写现实的人际关系外,还写了很多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星空是自然,山川草泽是自然,动物也是自然。地球上有大约150万种动物,其中许多都具有灵性,比如我们说的蛇、猴子、乌龟等,也包括猫头鹰。我小时候老听大人讲,“夜猫子叫,准没好事”,因此对这个动物记忆深刻——它不是个好鸟,一叫就会把一个人的魂魄叫走,准死人。
我一直想写写猫头鹰,这次《星空与半棵树》刚好大量涉及自然生态,猫头鹰的叫声,以及猫头鹰“痛失家园”的惨惨戚戚、唠唠叨叨,便有了意味。它与小说是互补的关系,也是“点穴”的关系。它企图与人类就自然问题、哲学问题开展对话,但人类都讨厌它的“烂嘴”。
另外,猫头鹰的眼睛在白天什么都看不见,到了夜晚又特别亮;再加上它的脖子能够旋转270度左右,几乎可以看到360度全景,它的观察就显得特别有象征意义。它不吉祥,人人见了都想驱赶,但它还是要叫,要发出有关死亡与不祥的警示。
小说里写人与动物的生命沟通,甚至转化,吴承恩、蒲松龄、卡夫卡们早就干过了。我们不过是对优秀小说传统的继承而已。《星空与半棵树》里的猫头鹰一直在寻找与人类的沟通方式,它要不是“二级保护动物”,可能早被打死一百回了。
中青报·中青网:乡村是当代小说的富矿,但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乡村,小说对乡村书写有什么变化?现在年轻读者也许对乡村已经陌生,这部小说对他们来说的阅读价值是什么?
陈彦:中国农村现在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城镇化让人口正在朝生活条件相对便利的地方集中;另一方面,随着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生态旅游蓬勃兴起,很多人也正在向自然生态的青山绿水回归。这个过程自然会发生各种阵痛、乡愁和新的希望愿景。
而文学恰恰有宽阔视角,有艺术表达的丰富性。我从来不觉得书写乡村或城市会成为小说阅读的障碍,关键在于对命运与人性的深度开掘,是不是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或一群生命有启示意义。
流落到荒岛上的鲁滨逊,所开展的生活面相,到底是海洋题材、猎人题材、手工业题材、还是农耕题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面临困境时的内心搏斗与期望。文学终归是人的学问。作家写出了一类人的生活和命运,会使更多人从中获得相通的情感和精神共鸣。文学的魅力,也正在这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