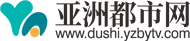读者在为丛报所营造的预备立宪氛围吸引后,便自然会对其相关的内容发生一定的兴趣,并会因此再于纸页中看到此类陌生的舶来概念时主动去寻找其定义和解释,或让之前由报中读到的分析释义再次浮现于脑中,使其对此之印象更为深刻。尽管丛报的读者主要是中上层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并不都具备西学素养,对一些名词和概念依旧难免陌生。而根据受众的社会分类论,因士绅身份成为预备立宪在民间施展之主力军的此类读者,自然会在选择和接受这类信息上更为注重而留意。故丛报中为预备立宪词汇做解释说明的言论总有用武之地以自证价值。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向读者普及西方宪政知识
遍览丛报中为数不少的政论文章,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都包含了对预备立宪相关概念的解释。虽然向读者阐释这些词汇的基础意义并不是此类言论的主要任务,这些文字能被写入篇章,也大半是因作者需要鼓吹其政见而被顺带提及。但这部分内容依旧在向读者普及预备立宪知识,并宣传立宪思想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随着丛报之前所传递与灌输之知识和思想,在不断开展和变动的预备立宪运动中得以为其所利用以解释相关之现象和言论后,读者会对丛报几乎隔三期差五号就有的,关于此类内容的提及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因为对理性的人来说,在新的物质形态中看见或认出自己的经验,是一种无需代价的生活雅兴。”其所论在丛报中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对立宪政体的简介
虽然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最后几年,全国有很多报刊和杂志都在不遗余力地鼓吹预备立宪,使得关于立宪的言论文章累牍连篇,如雪片一般盖地铺天般汇入舆论宣传的洪流。但民众对预备立宪的具体内容如立宪政体等,依旧知之甚少且含混不清这一状况,却是难以在一时之间因此而大有改观的。
比如丛报于1910年12月第二百五十五号所刊之《论资政院议员当知中国现在之政体》一文,单从题目即可令读者窥见此等情形之一斑。这说明在当时,即使在社会地位和知识水平都比较高的人士中,仍然存在难辨政体与国体之区别者,故需要被提醒“其一国最高主权之或在君主,或在人民之手者,则属于国体上之区别,与政体不相淆也”。
而关于政体方面,作者解释道“以现今学者最简明之区别论之,曰立预备立宪体,曰专制政体,无他名称也。”并称当下之中国“既非专制政体,亦非立预备立宪体”。而丛报中就立宪政体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从功能上着眼,认为立宪政体是一种从制度上平衡各方政治势力的存在。第二百二十二号《立宪国民之预备》一文就称“立宪制度者,政治势力冲突矛盾之制度也。”认为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其“盛衰倚伏”都是因为能支配国家的各派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互相作用的缘故,这样的冲突缠斗可谓是“岁不绝书”。
作者辩证地指出,一国之内的政治势力有所争斗是有弊有利,且过犹不及的。如果压制太过,则“社会奄奄无生人气,非国家之福。”若放任自流,就会因斗争过甚而使“主权失其统一,亦生国家之危害。”于是行使宪政的国家就需要立宪制度来“收容国内之各种政治势力,而不失其自由。”这里作者对立宪制度调控下的政治势力斗争中积极有利之一面予以肯定,认为不可为只图稳定但求无过而一刀抹杀,认为若“舍政权之争斗,则预备立宪寂然也。”
第二种是从制度上作解,声称立宪政体是一种从法律上规定国民责任与义务的设置。如第一百二十号所刊之《(杂说三)习惯与立宪预备之关系》,就在解释何种国民习惯有碍于预备立宪的同时,较为零散地阐释了此方面的观点,称“立宪者,所以使人人皆负责任,事事尽归法律者也。”认为立宪制度使得全体民众在法律的许可与准绳下得以“明定责任”而“监察他人”,并因此有了“履行责任之义务”,从而能够令预备立宪这“一国之事”能够“与一国之人,同力经营”。
(2)说明立宪之起源与起因
不仅就立宪政体是什么给出了一些解释,丛报亦向读者普及了立宪制度等宪政要素起源于英国这一常识,并称“为之母者英,导之先者美,推之激使全世界国民振起宪法之思想者,法国也。”且在立宪思想的传播上,丛报认为英国只起了间接的影响,法国和美国才是直接推波助澜者。
而关于预备立宪的起因,即“宪”为何而“立”上,从报的回答也基本一致。如第一百二十三号《论立宪国之精髓》,称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之所以都走上了宪政治国的道路,皆是为了反抗本国“数千年野蛮专制之磨劫积压”。正是因为“苦于君权之无限”的人民群众几十甚至数百年来坚持不懈地“冲突反抗,要求胁迫”,才为自己争夺而得到此“自由平等之权利”。刊登于第二百二十二号的《立宪国民之预备》亦认为立宪是东西各国君主与民众彼此宣战,前仆后继互洒颈中鲜血无数才结出之果实,并感叹清廷采取立宪仿行预备立宪,以改革避免革命,是“吾民顾安坐袖手,而享此千载一时之嘉会,毋乃易易!”
(3)指出立宪相比于专制有何不同
在对立宪有了初步的了解后,宪政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相对于其所要取代的旧日之专制有何区别,就成了读者十分关心的内容。而丛报对此也有不少解释,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首先是十分重视民众。如丛报第二百一十四号所刊之《论道德与立宪之关系》开篇便称“立宪政体行政最要之机关,在民不在君。”而第二百零一号《宪政之前途》一文更是在对专制大加批驳挞伐之后一转话锋,称“立宪则不然,盖必以多数国民之意思为准,则以多数国民之利害为从违,以多数国民之公认为效力。”可见丛报所言立宪制度之迥异于专制,其一便是将民众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其次是严格裁抑君权。“立宪之精髓,其要在限制君权,此立宪各国所同然者。”即使在具体的立法和行政上稍有不同,也不过是“所用与所行使其精髓之机关之不同耳”。这样的观点在丛报中很容易找到知音与共鸣,如第二百三十八期所刊登之《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就称“立宪政体之最可贵者,在其权限之严明。”正因为预备立宪国家的权责清正,所以君主可以,也只能“以神圣不侵之资格,不负政治上之责任”,而政府为了向君主负责,也不敢肆意弄权胡作非为。由此可知,丛报向读者展示的立宪制度中,君权被严格限制正是其对立于专制的关键之一。
最后是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君与民共变治于法律范围之内,严为权限,制为法典,而不得稍有所变。”是丛报中许多宣传预备立宪的作者同仁们所共识之真理,而“立宪之异于专制者,专制则权聚于一,立宪则权持以平”的高论,更是在第一百八十九号之《立宪以克己为体说》被再次提及呼告于民众。之后该文进一步解释,称立宪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家、君主和民众的权力和义务,是“校若画一,无所侵越,无可推诿”的。而在宪法和其他法律的严格监督下,举国无论谁人“虽欲自私,不敢违宪。”作者对此大为欣赏,称“苟其无此明文,则虽有圣贤之心,不能用保其不乱。”可见当时丛报舆论对立宪所提倡的“法律之下一律平等”这一对于专制独裁的突破与进步之赞许。
(4)对宪法一些特性简单的描述
宪法可谓是立宪的象征,也是预备立宪具体实施中的一个重大环节。虽然丛报对预备立宪的宣传主要是从整体和大局出发,较少就具体的政策和举措进行讨论,但依旧对宪法有零星的涉猎和描述,从而为读者勾勒出宪法应有的一些性质。首先是宪法为上下共尊之法,如丛报第一百八十六号所刊之《宪政编查馆编辑宪政大纲之意见》就曾提及,称“宪法者,君民共守之法也。”其他如“夫所谓宪法者,君与民均纳之于范围之中,而所当共同遵守者也”和“(宪法)为一国君主、官吏、人民所共守”之说亦能偶尔见于丛报,这与前文所提立宪制度中法律之下一切平等的原则互相配合,告诉读者立宪之后,君民都当以宪法为活动之根据与尺规。
其次是宪法为其他法律之根源,明确表意如第二百三十五号所登之《宪志日刊序例》,就有“宪法为众法之母,宪法不立,则众法皆隳”之言。此外还有“宪法者国家法律之根本,而人民公意之源泉也”及“(宪法)为一国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命令,更何法制,皆不能稍背宪法之原则”等论亦可寻觅于纸张之中,令读者知晓宪法地位之崇高。
最后还有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不可轻易修改更张。如第二百五十五号所登载之《论编订宪法与组织内阁》,就曾于文中着重强调预备立宪所立所用之宪法,应为万世不易之宪典。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夸张,但确实向读者传达了宪法作为根基之法,若要修改需重大之理由,须十万分慎重。
除此以外,丛报里关于宪法性质的描述中,也有一些出现了明显错误的地方。如第一百六十二号所载之《官绅熊范舆等联名上请愿书》就有“不知帝王不可侵犯,各国宪典,皆有明文”之谬说,显然作者没有限定所言之“宪典”为君主立宪国之宪法,使读者在理解时容易将美、法等无君主在位的民主共和国也统括进去。当然,根据全文可知,这很可能是熊范舆为首的请愿团以笃行立宪可令“责任负诸大臣,弹劾止于政府”从而使得皇室“其安富尊荣,比于专制国之君主,实又过之”为许愿之画饼,劝诱清廷踏实厉行预备立宪各事务,而故意为之。但不可否认,这样确实会在对宪法的认知上产生一些干扰和误导于读者。
就整体来看,丛报对立宪及其相关内容的解释虽然有所疏漏,甚至偶尔会有错谬之处,但其在解释宣传中很好地抓住了预备立宪的核心内容,就是利用宪法和其他制度来限制政府,从而保证国家运作的平衡与平稳。即“西方的宪法所追求的的价值目标是:通过制度的设计来实现宪法对对政府权力滥用的控制,并充分保障人权。”亦如萧功秦先生在其著作《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中就此的论述“立宪制度是这样一种制度:宪法是作为对政府的一种有效的和重要的制约机制而存在并起作用的,在立宪制度下,治理国家的人们必须受宪法各项条款的约束。宪法是政府和执政者行使权力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由此可见丛报在此方面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吴爱萍:《从康梁到孙中山——清末民初宪政理念与实践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3.李秀清:《所谓宪政——清末民初立宪理路论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