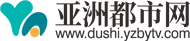年岁深刻了,岁月却安排我返回童年,以专业的名义,职业的名义,复活天真和滑稽。
大学毕业,副系主任找我谈话。
“怎么样啊,蛮好的吧,当大学老师了。”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我笑着,很恭敬地点头,想张开嘴,回复出心里的激动,却不能立刻找到自然的词语、句子。
副系主任说:“蛮好,蛮好,你这个小青年蛮好的,要好好的啊!”
副系主任是一个语言很生活的人。
毕业前我去名牌中学实习,上完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听课的校长热情地希望我分配到他们学校,结果被拦住了告知,这个学生学校已经有了安排,拦住校长的就是副系主任,他当时也在听课。
副系主任告诉我,以后就教现代文学了。他还提到我实习时讲《最后一次讲演》的情景,说:“蛮好蛮好,很像闻一多。”他说,以后好好研究鲁迅、闻一多、茅盾、巴金、郭沫若……很有前途的。
我开始阅读现代文学史,专心致志,迅速地让自己现代文学起来。记着里面的各种争论、阵营,让自己有重的感觉。它是为人生、为社会,甚至为斗争的文学,自有磅礴的使命,还有摩拳擦掌,辛辣,凌厉……它是扛着天空和大地的,轻飘飘的不是鸳鸯蝴蝶派,也是无关紧要派,不上台面。这是我那时被教育的认识。我放一本鲁迅的书在桌上,常看他的照片,确信他雕刻般的神情便是我以后的课堂神情,暗自觉得一定帅透。
可是,还没有等我正式备课,写讲义,因为写了一篇儿童角色的小说得了儿童文学奖,领完奖回来,副系主任突然通知我,去北京的一所大学学习儿童文学,他说,这是学校郑重决定的,蛮好的,学习好了,回来把课开起来,师范大学要有儿童文学课,可以坐火车卧铺去,“怎么样啊?”他笑嘻嘻地看着我,意味却严肃。
我毫无准备,却依然还是点头,没有问,回来以后现代文学还要不要上,还要不要讲《彷徨》和《呐喊》。我那时趁着《最后一次讲演》的“回声”,甚至把闻一多的《死水》也背流利了:“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其实,文学的基础视野,童年家中的书橱都已为我摆放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里的作家,很多都见过名字。父母不是学文学的,但都是一流的文学阅读者,半个红学家的爷爷读过的书也在书橱里。母亲如果轮到现在的年月,一定是一个“资深”阅读推广人,她读完一本长篇小说,常常往中学生的我面前一推:“你可以读一读!”所以,《子夜》《家》上初一时已经草草读过。六七岁时玩耍般地从书橱里抽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摸着讲究的封面,记得那蓝色,知道了有一个斯大林文学奖,它得的是二等奖,就懵懂地想,一定还有一等奖,它是竖排的字,端在手中是一个厚厚的远方。艾青、胡风的书,甚至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都捧起过又放下。何况后来当知青的时候,因为写出过幼稚文学,登入书刊,被送进国家大词典编写组,干着零碎文字活,挑选词目的书恰好正是中国的现代文学,读了很多,好似正为了准备着这一天,迎候着它的到来!
可是,现在却又被改向了。
在这样的事情上,我向来不多问,知道了一就可以了,不好意思问二,问三,习惯戛然而止,习惯响应,习惯立即开心起来,心满意足往前走,腿脚抬得很高,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从前线复员归乡的士兵,一直往前走,走得忘记前因后果,只看见脚下路。
我是乘13次特快卧铺去北京的。那个年月,一个普通人,一个助教,乘特快列车卧铺,是好光荣的,有点了不起!乘了一次,便知道有了飞机座的新车型,也是特快,老式的卧铺票价44元,飞机座37元,于是宁可改乘37元飞机座,车厢大气、明亮,座位可以360度转动,虽不可以躺下了睡,但感觉高级,是那个年代的顶端,坐下了便想抒情,车窗外的任何闪过,都如诗,夜晚也是看着那闪过的黑黑的诗,句句耀眼,分秒都美。那时,我不止一刻想到副系主任,他对我说的话,代表学校对我的安排,以及陡然的变化。现代文学也好,儿童文学也好,都令我澎湃,都如他的口头语:蛮好的,蛮好的,真是蛮好的!
车厢人很少,对座是一个穿着讲究的香港人,夜晚,拿出一包三五牌香烟,友好地问我,要不要抽一根。在此之前,我只抽过一口海鸥牌香烟,是下乡第一天晚上,读《资本论》,点燃了,抽了一口,把崭新的帐子烧了一个洞,从此看见香烟无半点感觉。现在有了感觉,但是不好意思接受别人的客气。如果抽了,那窗外的黑就更一闪一闪星语心愿了,那时还没有《星语心愿》!
我跟着教授学习了儿童文学,乘坐特快列车返回学校,飞机座车厢已经取消,问售票窗口,因为不能躺平了睡,票价又比坐票贵,不被欢迎……我成为了大学文科中一个最小学科的老师,讲课,写作,浅语,轻快,梦幻,温暖……兴致雀跃。以为年岁深刻了,岁月却安排我返回童年,以专业的名义,职业的名义,复活天真和滑稽,绿野仙踪,秘密花园,木偶成长,骑鹅旅行……以文学的名义、生命的名义、浪漫主义精神的名义,带领着学校阶梯的课堂、社会会场的课堂,复活单纯和诗意……
几十年间,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我就这样被安排了度过美好,美好得日常又文艺,常常遇上故事。
那一回在一个海边城市,对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们讲童话和阅读。一个小学生女孩,捧着鲜花,远远站在台下,从开始到结束。我请她上台,她走到我面前,一言不语。我问她,怎么不说话?陪她的老师说,她喜欢你写的故事,看新闻知道你来,想看见你,请妈妈向校长请了假,我陪她来。她以为你的年龄和他们一样大,但你怎么是这样的?可是你写的活蹦乱跳怎么又会和他们一模一样?她不明白了!
那一刻,我是应该滑稽地哈哈大笑的,可是却感动得深切,有些自怜,更是自豪,眼眶湿润:从满头黑发到满头白发,天真的儿童们读到的却依然是一个满头黑发,是一个如同他们的小孩子。
全场都鼓掌。
这真是蛮好,特别好,我没有机会告诉副系主任,他远行了。也没有机会对我的大学叙述。
都是他们的美好安排,我依然童年。(梅子涵)